
来源:网络整理 时间:2014-04-20 16:36:36 阅读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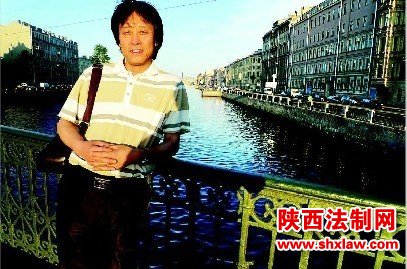
李云集近照
李云集西安美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陕西省美术家协会理事、黄土画派艺术研究院画家、陕西国画院、西安中国画院外聘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陕西创作中心艺术创作部主任、陕西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艺委会副主席、陕西省高等教育学会艺术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山水画研究会副主席、陕西省文史馆研究员。
近年来先后为中国驻外使、领馆,北京人民大会堂陕西厅,陕西国宾馆,陕西大会堂等单位创作众多重要画作,颇具影响力。李云集官方网站:http://www.liyunji.com如果说,中国是一个传统文化的国度,那么文化国度之灵魂便是诗与绘画。而诗与绘画的诞生基础,则是人们关照自然的山水情结所致。
打开中国美术史,林林总总、历朝历代、名家辈出,而占比例之高者,当以山水画为最。难怪古人有云:“画分十三科,山水为上。”在这里我们暂不究其什么原因,就这分类的言辞和假设的规定性而言,毫无疑问,它为我们传递了一个细微而又关键的信息,即喜山好水在中国文化人的内心深处是一种淡淡的渴望与理想。
我们都知道南宋时的宗炳,善书画、作琴书、好山水,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即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象。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宗炳指出的自然山水的美,是为说明山水画的美,他在《画山水序》中说,“余眷恋庐、衡,契阔荆,巫、不知老之将至。愧不能凝气怡身,伤踮石门之流,于是画象布色,构兹云岭。凡所游历,皆画图悬挂于壁上,坐卧向之。其高雅情怀至极矣。”这些认识与行为,我们不能不说,他是一位自然山水的痴情者。他“画象布色,构兹云岭”作山水画的目的是为什么?因为他眷恋着曾游历过的名山大川,因为那时他还年轻,不知老之将至。愧恨自己未能凝神静气以养身。践履石门之流以后病倒了,想起来不禁哀伤。现在只有观山水画以代游履。
诗人袁枚,是清代性灵诗说的创始人,也是一个酷爱自然山水之人,以亲近大自然为终身乐事。乾隆二十三年,时隐居南京小仓山随园,曾作小诗一首云:“连霄风雨恶,蓬户不轻开。山似相思久,推窗扑面来。”诗人前二句写风雨连霄,来势之猛,门窗都难以打开,只因“风雨恶”而一直被关在屋内,如处牢笼。一个“恶”字既写出风雨之猛,亦写出诗人内心的感受以及当时的情景。而后两句则突然间“柳暗花明”写风停雨霁。诗人终于可以打开窗户欣赏大自然的清新风光了。但诗人不写自己,却掉转笔头写青山思念,把着眼点放在自然之山,将山以人格化,因此,一但见诗人推窗,即扑面而来,迫不急待。这时的山在诗人的笔下变静为动,化无情为有情。诗人之与山,山之与诗人,不能你我。
无论宗炳还是袁枚,只是我们文化的国度中许多人所感受到的典型代表而已。而从上述两人对于自然的感受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和寻找出,自然山水是中国文人灵魂的追求,是他们实现自我的唯一通道。他们内心深处有着一个共同的自然山水情结。而这一情结,使得从人生自然、社会等等不同层面都或多或少弥漫于这种自然山水的气氛之中。可以毫不掩饰的说,作为人的生命本身,要脱离开现实生活的缠绕,去实现人生的理想,只能寄情,放纵于自然的山山水水,而人生过程的圆满结局及最后的归宿也只能在自然山水状态中去寻求。由此,中国的山水画,是有关自然的山水情结所致。其作品的内涵与外延须更加自然,在自然中更乐于隐藏着深深的人格化的东西。在大自然的深处,探究其中的玄妙、神秘与至美,使作品给人以绝妙的含蓄和感受。
元代的黄公望在他的画诀中曾说:“凡经营下笔,必合天地,而所谓天地,谓一幅半尺之上,上留天之位,下留地之位,中间方位立意定景。”此时的天地,从表意看似乎只是一个简单的关于构图问题的具体理解,诸如当展素携笔,而对作画时的前期判断,应注意上下、左右、大小、分黑布白等等具体的形式法则。而内在的确是已设定的法则早已规定你必须沿着这设想的路走下去,即所谓的理想之境。而这理想之境是经过若干代人的努力与总结,是约定俗成的一种人格化了的构图要旨。当然这样的构图,从心理上说是一种假定的理想与实现的渠道,依次进入,便不会偏离主流。
“山水先理会大山为主峰,主峰已定,方作依次,近者大者,远者小者,以其一境,立之于此。故曰:主峰如君臣上下也。”
“林木先理会一大松,名为宗老,宗老已定,以次方作杂窠小卉,女萝碎石,以具一山之表。宗老如君子小人也。”
“大松、大石,必画于大岸大坡之上,不可作于浅滩平渚之地,松树不见根,喻君子在野,杂树喻小人峥嵘。”
此时所言之景,已经远远超越绘画本身的自然属性,完完全全地把自然的生态荣枯喻以人格化,诸如君臣之类、宗老之类、君子与小人之类,字里行间,无一不渗透着对于真实自然的一种极端超越的心理定势。当你手握寸毫,饱蘸沉墨之时,面对的不仅仅是普通的一山、一石、一树。而是一种自然之理与人生之理的双重整合的特殊要求,更是中国文人的审美理想,最终应该是全人类共同期待和永生追求的人世间最高之理想境界了。
古人曰:“山有多高,水有多长。”传统山水画关于水的描写,同样也有严格的规范。言及石为山水之骨,但水又为石之骨,因为水性至柔,排山穿石,力撼巨灵,姿态横生。所有一切,莫刚于水。自古至今,聪慧的大师们在艺术创作和生命的延续过程中,把水也趋于人格化来理解认识,水之利害则兼而有之,关键是我们怎样去疏导利用,使水真正做到便利于民。即“上善若水”。在绘画形式上,不能随使妄加,而要切合情与理不同的两个层面,使自然之水升华为人文之水。如店舍依溪大依水围,依溪以近水,不依水围以为害,或有依水围者,必水之无害也。以此为忌,同样也是重要的一个绘画法法则。这种理想的思维定势,其内在的核心,还应归属于文化人对于自然山水痴情的眷恋和向往。
就以上的理解和分析,我们不难从中发现,历史渊源流长而深厚的传统山水画,经过历代各朝、名家大师不懈的努力,在前人的基础上,或抑、或扬;或褒、或贬,几经积累已呈现出艺术品评的相对稳定性,而这种稳定性的不断伸延,直接受益的是程式性很强的传统山水画作品本身。
五代两宋时期,美术史家往往把这个时代称作为传统山水画创作的高峰期。无论五代时期的南方山水画,还是北方山水画,无论关仝、李成、范宽,或是荆浩、董源、巨然,或北方,或南方,而山水画的实质面貌都已趋于完善和成熟。或古木、长松、杂树、灌木;或高山、飞泉、流水;或山石突兀、低矮山丘、平沙浅渚、洲汀掩映;或平淡天真、轻烟淡峦、气象湿润;雄伟峻厚、石质坚凝、风骨峭拔。诸如此类,绘画的多种要素已趋成熟和完善。
一般的讲,当传统山水画发展至元代,由于当时绘画新材料的出现,在形式上是元代画家发生变化的基础,在这里,就我本人的看法,则不尽相同。所谓元代四大名家,我们从王蒙、黄公望、倪云林、赵孟钏鞔吕吹淖髌房矗谡蹇蚣芗敖峁股希杂谒稳说某淌椒⒄够故浅倩旱摹U庋睦斫馐谴庸惴阂庖迳先タ矗浔士荨⒛⑸幔溆幸菡叩母哐偶白匀坏牧秩咧拢退嘉馐叮匀挥屑坛泻湍》轮印U庋褪俏宜档某倩骸5比唬庵殖倩菏窍喽缘模⒎嵌栽婊姆⒄钩址穸ㄌ龋皇谴铀嘉系囊恢肿萆罾斫狻C髑逯实囊帐跫叶荚诓煌潭壬涎刈殴湃说纳竺览硐耄粤翟谧匀坏恼嫔秸嫠洌倘缫豢趴乓鄣男滦牵抑啵杀鹬无樱嗷ソ淮矶嘀梢桓霾永枚曰偷囊帐跏澜纾成剿淖陨矸⒄梗谡飧鍪贝幸擦芾炀≈路⒄沟郊蓿裙湃烁髯匀弧⒆晕摇⑺嬉狻;谝陨隙灾泄成剿纳竺览硐耄竺佬问揭约俺淌降睦斫夂头治觯颐遣坏闯觯泄成剿姆⑸⒎⒄购统墒斓睦饭旒#乙彩枥沓隼硐胗胄问剑ǔ淌降囊蚬叵担缛粑颐抢渚捕蜕频娜ダ斫夂退蜒埃馊肿刺衅浠ゲ剐院拖嘁佬裕褂蟹⒄剐浴H肿刺娜魏我恢侄际墙⒃谙嗷ト诤稀⒎纸狻⑸傅幕∩隙⑸浠摹6魑滓侍馓岢龅纳竺览硐朐蚴钦贾鞯嘉恢玫木窀叩亍H绻瞪竺览硐氲氖迪郑侨死嘁帐跎某绺吖樗蓿敲矗竺佬问降姆ㄔ蛟擞茫闶前镏迪掷硐氲淖匀灰劳兴冢佣陨竺佬问轿劳腥ス菇ㄒ帐醭淌降纳捎敕⒄埂H叩南嗷ト诤希怪泄成剿庵忠帐跎竺赖奶卣鞒晌髦迹⑶沂沟迷谡庖晃幕袂卤怀谱鞴獾拇成剿鞔两癫⒎⒀锕獯蟆



